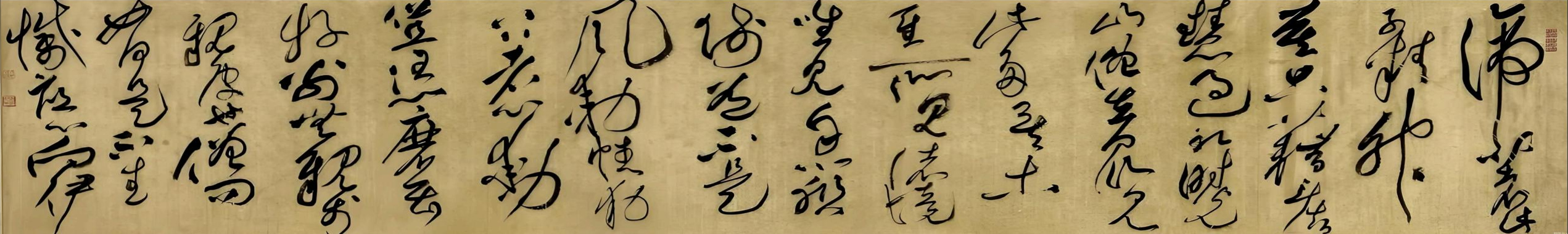圣人之言——论孔子语言之根据、发生与朝向
作者:颜清辉
来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摘 要]如何面对孔子之语言?既不落入西方诸多主义、理论、概念的陷阱之中,又能在今天的语境中重审或重现孔子语言之实质。可行的方法或许是,以敬慎的态度深入地厘清文本,以便重新进入孔子的语境之中,从而贴近其语言。研究发现,在相关文本精炼、深邃、感染性极强的表达中,孔子之语言既精微又广大。其语言不是逻格斯,它并不依靠推理,也不是为了解释世界,更不会抽象。而是敬恪往古圣王之言,并以之为典范,从而召唤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德性。在语言的召唤之下,将人导向成德、成人乃至成圣的具体行动之中。当语言达成其使命之际,便自行隐退归于无言,至此,整个宇宙便化现为天德的恒久运动——道。最终,语言又重新显现,以全无意指的方式表现为对 “ 天道 ” 的赞叹。
[关键词]孔子;语言;德性;天道
[作者简介]颜清辉(1986-),男,湖南冷水江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宋明理学和中医思想史。
向来论者极赞庄子善用 “ 三言 ” ,以为 “ 寓言 ” “ 重言 ” “ 卮言 ” 可尽语言之妙;又或者迷于禅说,游戏于隐喻、棒喝之机锋中,以为 “ 语为义指,语非为义 ” 足以打破语言之藩篱。殊不知,孔子之语言看似 “ 无头柄 ” 【1】,实则严谨精微;看似平实,实则广大高明。汉学家安乐哲即认为孔子是个 “ 沟通大师 ” 【2】。关于孔子语言的研究者们,除郝大维、安乐哲、陈汉生等主观上试图关注孔子整体语境的研究者之外,多数虽指出 “ 先秦语言哲学肇始于孔子 ” 【3】,然在实际研究中,却多停留于 “ 正名 ” 之研究,亦或拘泥 “ 名实 ” “ 言意 ” 等几组碎片化概念的辨析,间或能注意 “ 无言 ” 之问题,可并没有考虑孔子语言之整体运作。本文通过对相关文本的深入阅读,考察孔子语言结构及其在语言实践中的具体展开方式,希望借此进入孔子之语言世界,从而体认其语言的真谛。
一、语言根据:正名
《论语·子路篇》记子路问孔子 “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 关于 “ 正名 ” ,历史上的注释者们争论纷纭。但不论是说 “ 正书字 ” 【4】,还是 “ 正名分 ” 【5】,又或是 “ 正百事之名 ” 【6】,乃至如当今学者所释之 “ 概念 ” “ 范畴 ” 【7】,均非语言上的意义,很多情况之下甚至已经脱离了孔子的语境。本文的任务既是为讨论孔子语言,所以应当问的是, “ 正名 ” 是否能够成为其语言结构中的一环?如果可以,那么在语言结构中的意义是什么?欲回答此问题,必先进入孔子之语境,方能厘清 “ 正名 ” 之实义。且看: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8】
温海明曾强调:“ 以名出言,以言行事。” 【9】即从 “ 名 ” 的安立出发,经由言语的发生,最终让行动有所依藉。是以,在 “ 名—言—行 ” 的发生秩序中,位于中心者恰恰是 “ 言 ” 【10】。若借此以检省思想史上关于 “ 正名 ” 之阐释,会发现多数取消了 “ 言 ” 原本该有的中枢地位,导致的结果是直接由 “ 名域 ” 跨入 “ 行域 ” 。换言之,语言本有的重要意义被抹除。所以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孔子只 “ 重视名的政治伦理内涵 ” 【11】,或者说 “ 只重视观点和立场而不看重‘真理内涵’ ” 【12】。甚至某些学者不无鄙夷地认为,孔子用 “ 正名 ” 堵住了悠悠天下之 “ 言 ” ,以至沉沦为一种坚固的 “ 话语权威 ” 【13】!
“ 君子名之必可言。” 不仅要 “ 可言 ” ,而且要 “ 言顺 ” ,这正是 “ 名 ” 的任务。反过来说,若欲 “ 可言 ” 则必先 “ 有名 ” ,老子亦云:“ 始制有名 ” 。“ 言 ” 当以 “ 名 ” 为前提或者根据。但孔子并未明言 “ 名 ” 之具体所指,因为孔子并非在超验或者抽象的意义上来使用 “ 名 ” 之一词,而是日常意义。如 “ 名 ” 在 “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中指名字、称呼,在 “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 中指名声,在 “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 中则是形容、称赞之意。总言之, “ 名 ” 既有名词性的名称、名声,又内蕴动词性的指称——命名行动;是故《说文》云:“ 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当 “ 名 ” 作为名词性的称谓时,意义在于:其一,使对象物向人显露自身,即许慎 “ 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 之隐喻。物本至赜, “ 冥不相见 ” ,因 “ 名 ” 方可以显现。其二,指向某种恒常之性。毕竟物事变动,上下无常,因 “ 名 ” 方可于流转中得以 “ 箍定 ” ,守住其自身之所是。名家及黄老对此阐述得比较清楚,如《尹文子·大道上》曰:“ 名以定事 ” ,又《黄帝四经·原道》谓:“ 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 ” 。其三,意味着某种分别与判断。董仲舒谓:“ 名者,所以别物也。” 【14】万有不齐,因 “ 名 ” 而可以各归其类、各得其所,故董子又云 “ 事各顺于名 ” 【15】。
然而当继续追问作为动词性的 “ 名 ” 之时,却发现孔子并没作过多解释。他似乎并不打算探问命名的依据,以至于后之诸子争论无休。这难道是孔子对此问题的无知吗?或许正是因他清楚问题的复杂性,才刻意选择规避,转而强调 “ 名 ” 要 “ 正 ” ?
不论是强调因 “ 真 ” (实)以制 “ 名 ” 的 “ 理想派 ” ,还是 “ 约命 ” 成 “ 名 ” 的现实派【16】,都将碰到来自其自身的诘难。前者的问题在于,如果 “ 真 ” 先在于 “ 名 ” ,那么谁知道这个 “ 真 ” ?或者说谁定的这个 “ 真 ” ?“ 真 ” 毕竟并不主动向人显现,它必须借 “ 名 ” 才能生成意义。若无 “ 名 ” ,如何识得 “ 真 ” !所以, “ 真 ” 以制 “ 名 ” ,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权利幻象;而后者的问题在于,约定俗成之名是在同一类型的历史文化之中生出来并被共同认可与使用,即依地、依时、依族类而 “ 约命 ” 以成。也就是说, “ 约命之名 ” 仅在特定的时空中对特定的人群才有意义,当时代变化、族类往来乃至更大规模文化冲突之时,便会显示出它的滞后性与窒碍性。因其无法适机的调整、重塑自身以适应语境之变化,反而让 “ 名 ” 陷入混乱之中。这正是孔子所面对的、亦或是最根本的问题——周文疲弊、礼崩乐坏,旧有之 “ 名 ” 已无能撑起现存之世界!陈启云便认为,孔子所面临的正是一场 “ 语言危机 ” 【17】。
追问命名的根据不仅毫无意义,反而会衍生出更多问题,故不如将其悬置。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 “ ‘名’‘’‘指涉’功能或角色本身就是它的‘名’ ” 【18】。所以,孔子并不去追寻 “ 名 ” 的起源问题,转而向 “ 名 ” 自身下功夫:以 “ 正名 ” 为 “ 名 ” 立法。“ 正名 ” 之目的,是为了 “ 名正 ” 。无论以何种方式所得之 “ 名 ” ,皆须得其 “ 正 ” ,才具备合法性。也就是说,孔子把问题转换了,把原本为了 “ 获得对世界万物的恰当指称 ” 【19】之名,置换成 “ 名 ” 应当如何 “ 正 ” 的问题。
所谓 “ 正 ” 者,指人以修剪裁成之功夫,使自身或某物(事)成其所是,安于其所。这就意味着 “ 正名 ” 必然横跨两端:一端是作为主语的人,且是具备德性的人。人必先修身正己,具备君子之德,才可以有正当的 “ 名 ” 。故云 “ 君子名之 ” ,又云 “ 君子去仁,呜呼成名 ” ,《礼记·学记》亦云 “ 君子比物丑类 ” 。反之,若无君子之德,便不足以 “ 名 ” 。“ 正名 ” 真正的主体,恰恰是 “ 德 ” ;另一端是 “ 名 ” ,因德性而成之 “ 名 ” ,便不再滞留于概念、定义,并且同样也获得德性。“ 名 ” 实质上,是 “ 德之名 ” ,所带出的物(事)同样的也具备德性。由 “ 名 ” 而筑基的世界,也将是德性充周之世界!与此同时, “ 名 ” 因其自身所蕴之德,又可将言说者引向德性修养之途。于是, “ 正名 ” 之下人、名两端齐归于正,合于德。孔子之后,孟子深得此精神。孟子并不像荀子那么关心如何 “ 制名 ” 的问题,而是极倡 “ 正心 ” ,以之 “ 正名 ” 。近代鸿儒马一浮亦谓:“ 正名者,正其心也。” 【20】
换言之, “ 正名 ” 远非 “ 名实之辨 ” 的问题,亦非维护固有社会阶层,更不是拥护专制统治。而是说,孔子以 “ 正名 ” 的方式,使得原本作为语言根基的 “ 名 ” 让位于 “ 德 ” 。“ 德 ” 成为语言真正的根据,故曰 “ 有德者,必有言 ” 。虽然孔子紧接着说 “ 有言者,不必有德 ” ,但言说若不以 “ 德 ” 为根据,那么君子便会 “ 耻有其辞而无其德 ” 【21】,最终落入孔子的批判之中—— “ 巧言乱德 ” 。
《论语》之终章《尧曰》云:“ 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根本原因在于,语言与人原本深切关联。这里,既不是单方面的 “ 语言说人 ” ,更不是人在工具性地使用语言,而是说人与语言相互嵌合,相互激发。语言牵引着人回向作为根据的 “ 德 ” ,人则凭借着语言将原本隐匿的 “ 德 ” 显现出来并充阔于世界之中。
二、语言实践:慎言与取譬
语言的根据是 “ 德 ” ,其使命是让德能够如实显现。所以,可以说语言的本质是 “ 德言 ” 【22】。如《乾卦·文言》曰 “ 修辞立其诚 ” ,又云 “ 出其言善 ” 。《卫灵公》云 “ 言忠信 ” ,《季氏》云 “ 言思忠 ” ,《泰伯》云 “ 其言也善 ” 。那么,我们接下来当追问的是,什么是 “ 德言 ” ?“ 德言 ” 如何实现?
《康诰》曰:“ 绍闻,衣德言。” 孙星衍疏云:“ 言今之人,将在敬述文王,继其旧闻,依其德言。” 【23】意思是说, “ 圣人之言 ” 即是 “ 德言 ” 。《易·大畜》云:“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基于语言的这一使命,语言会对真正的言说者提出要求,要求其对语言存有敬畏,是故孔子极为强调 “ 畏圣人之言 ” 。孔子终身所奉行与践履的正是以其敬畏,一方面谨恪 “ 圣人之言 ” ,以 “ 述而不作 ” 的方式节制自身之言说,为免偏离 “ 德言 ” ;另一方面践行 “ 雅言 ” “ 祖述尧舜 ” ,以确保言说始终浸润于 “ 德言 ” 之中,得其滋养。可以说,敬畏是对 “ 德言 ” 最根本的守护,也是对语言最根本的要求。
当 “ 德言 ” 生长出来充满盈溢于语言所建筑的世界之中,即当语言据德以顺遂发生之时,其要求亦随之而变,由 “ 敬 ” 而转入 “ 慎 ” 。《国语·周语》云:“ 慎,德之守也。” 慎之为言顺也。“ 慎言 ” 即遵循、依顺语言之本质—— “ 德言 ” ,而如其所是的发生,以确保言说不至于散乱、异化。故《系辞》云:“ 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 “ 慎言 ” 不仅指言说者的态度,更重要的是 “ 慎言 ” 必须因语言之本质而裁成其言说,以看护言说的发生,使其如其所是地充满、洋溢于语言世界中。
“ 慎言 ” 其实是语言自身的真实发生方式,是语言在其展开时自我赋予的基本原则。因此,孔子极为强调言说应当审慎。如《学而篇》中云:“ 敏于事而慎于言。” 《为政篇》谓:“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 以及与 “ 慎言 ” 相类者,如 “ 讷于言 ” “ 其言也讱 ” “ 巽与之言 ” “ 危言 ” “ 言逊 ” 等。又《易·颐》曰 “ 君子以慎言语 ” ,《坤》曰 “ 盖言谨也 ” ,《中庸》谓 “ 庸言之谨 ” 。而与 “ 慎言 ” 相反者,正是孔子多处批判的 “ 巧言 ” ,因为 “ 巧言乱德 ” 。没有经过敬慎的言说,足以败坏德性,便无法如其所是地成为真正的语言。“ 慎言 ” 指向以下两个方面。
(一)言说者的审慎
第一,孔子认为:言说者的生命状态与其言说应当内外一致。是以《为政》云 “ 色难 ” ,《阳货》云 “ 色厉而内荏 ” 。“ 色 ” 并非外来的虚伪巧饰,而是言说者本真状态的自然彰显,是内在之德形诸于外。如《大学》云 “ 诚于中形于外 ” ,《泰伯》云 “ 正颜色,斯近信也矣 ” 。倘若无德,却巧饰其色,则内外相悖,便落入孔子深恶痛绝的 “ 巧言令色 ” 中。所以,当孔子说 “ 察言而观色 ” 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语言与言说者整体状态的呈现应当一致。
第二,言说者之言说与言说对象(倾听者或受教者)的状态应当一致。是故《季氏》云 “ 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 ,《述而》云 “ 互乡难与言 ” 。此精神在《论语》的载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诸门徒之问仁,孔子却各因其人(非因其问)而立其说。《卫灵公》云:“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言说对象已经准备好,呈现为某种状态,此时需要抛出相应的语言,以护持乃至牵引对象进入语言的本质之中。因为,语言的本质可以召唤、接引对象回向对自身的照看,使其朝向于德。如果此时不抛出语言,或者抛出的语言不能与对象相感应,那么对象将与德失之交臂,最终错失回归其本性的机会;如果语言已被抛出,可对象却尚未做好准备,那么,语言便会与对象擦身而过落入虚空,并不会彰显任何东西,如同未曾发生。
第三,言说应当与言说者所处的位置一致。《乡党》记孔子:
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24】
言说者总是在某个具体的位置上言说,然而位置萦绕着言说的气氛所形成的势,会影响(引导或压制)语言的发生,很有可能便沦为一种权利话语。但是真正的言说者,恰恰能够将自身退出,从而消解位势,便不能成为某种压制。更重要的是 “ 无我 ” 所让出的空白可以迎纳纯德,从而更好地护持语言的发生。
(二)语言自身运作的时机性要求言说审慎
语言总处于发生之中,流动不居,倘若言说不能恰如其时地进入语言之中并与之嵌合,则言说终究不能得其本性而成为语言。《季氏》云: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25】
及,时也。就是说,如果语言尚未发生,而言说却早已开始,这样的言说便不能称之为语言,孔子命其为 “ 躁 ” 。言说无法安住于语言中,即谓之 “ 躁 ”【26】;又或者,语言已然发生,言说却还未开始,那么语言将归于消隐。语言发生呈现出的时机性,要求言说者对此时机有着深刻的觉知。必如此,言说才能 “ 与时偕行 ” 、是其所是——成为语言。故《宪问》云:“ 夫子时然后言。”
孔子云:“ 言不可不慎也。” 然而 “ 慎言 ” 在其顺遵中,难免成为某种禁戒,沦为某种坚硬的律令,最终塌缩为狭小的封闭空间,而丧失开放与创造的可能。更为严重的是, “ 慎言 ” 或许会桎梏语言原本浩荡的生命,而显得拘谨、干瘪,以至于不再具有感动之能,反而违背其将德引入世界的初衷。所以,语言因于自身,势必提出另一个要求——与 “ 慎言 ” 相反却足以相成——以确保语言能够如其本质的顺遂发生。这个要求就是:取譬。
如同对 “ 慎言 ” 的重视,孔子亦极为强调 “ 取譬 ” 的意义。《雍也篇》中孔子教导子贡时,云:“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 。《说文》云:“ 譬,喻也。” 取譬亦即譬喻,此时或许会让人想起庄子三言之 “ 寓言 ” 。“ 寓言 ” 自然也会涉及譬喻,但与孔子之 “ 取譬 ” 在取向上有着本质的差异。揭示这个差异,对理解孔子的 “ 取譬 ” 极为重要。
庄子自谓 “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 郭象注云:“ 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 【27】缘何要借之于外?陆德明解释说:“ 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 【28】陆德明的意思是,原本不见信于人,如果能借之于他人、他物,便足以变得可信。不过,这倒也符合普通民众的心理。然而孔子的心志却是 “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 ,是 “ 遯世不见知而不悔 ” 。以孔子的观点来看,陆德明解释庄子的 “ 寓言 ” 无异于谄媚,恰恰成为孔子深恶痛绝的 “ 乡愿 ” 与 “ 巧言 ” 。以至于后世儒生,对 “ 寓言 ” 难免会有诸多鄙视与讽刺。如《唐语林》在使用 “ 寓言 ” 之意时,云:“ 元佑献诗十首,其词猥陋,皆寓言嬖幸,而意及兵戍 ” 。即便积极地去理解 “ 寓言 ” ,亦仅在于 “ 藉外论之 ” 可以增长德性之外的知识见闻而已。如《双溪杂记》之所云:“ 后世山林隐逸之士有所纪述,若无统理,然即属事寓言,亦足以广见闻而资智识。” 【29】
可问题是,倘若语言自身不足以信,仅凭 “ 外论 ” 的堆积便足以见信的话,这无异于是在说语言本身并不可信,而必 “ 由乎人也哉 ” 【30】!“ 有言不信,尚口乃穷 ” ,孔子再三强调的是 “ 言忠信 ” ,认为 “ 信 ” 是语言本有之物。故云 “ 言而有信 ” ,而非 “ 言而求信 ” 。既然 “ 不愿乎其外 ” ,又岂可外求?所以对于陆德明之流释庄子 “ 寓言 ” 的思维方式,难免有所激愤却又无可奈何,不得不悲叹道:“ 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 。有此对比,再来看孔子所讲的取譬,会更为明晰。
事物恒转,变动不居,语言亦永恒流动。我们要问的是,若仅以A之名,是否能充分表达A原本指称的物(X)呢?既然X在流转之中,那么A所能表达的只可能是X的当下。所以,对X来说,B、C、D……或许均可以表达。孔子之语言实践将此展现得淋漓尽致。如《为政》 “ 譬如北辰 ” ,是以北辰之情状来揭示为政之核心。《子罕》 “ 譬如为山 ” “ 譬如平地 ” ,以言进德在我。《阳货》 “ 譬诸小人 ” ,以掘墙凿洞之盗贼言外强而内虚者。以上几例,皆非停留于A以言X,而是以A之外的其他物事来谈论X。这并不是说A不足以信,需借其他物证信。而是说,A原本就只是语言生发出来的一个截面,用B、用C同样也是对X的言说。并且对于X来说,仅知A并不全面。是以《述而》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朱子《集注》谓:“ 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意。” “ 四隅 ” 即以四方为结界,相互联结围出物之整体情状。《公冶长》中子贡极赞颜回 “ 闻一以知十 ” 。《说文》云:“ 十,数之具也。” “ 十 ” 即整体之谓也。物被语言带出来时,实际上是在语言中整体显现,本未被切割成碎片,老子亦云:“ 大制不割 ” 。这就注定语言必定对 “ 非此即彼 ” 的表达方式的拒绝。
“ 取譬 ” 得以成立的缘由,正在于必得语言之整体,方可以真正地认识整全之物。并且因为 “ 取譬 ” ,语言得以保持永久敞开之势。因为 “ 取譬 ” ,破碎之言说均被保持在语言整体之中;因为 “ 取譬 ” ,物虽散,而亦不失其朴。
物虽是经由语言向人显现,其根本却在于人物之相遇,即人物之间的感通。如无感通,两者相否绝,语言便无缘而生,物终静自于沉寂中沉寂。所以当语言兴起时,实质上已经是人物无碍、感而遂通。人物相遭遇之际,语言顿然兴起,然此时,语言尚处懵懂萌发之状,尚无方所。人对此情状或有感知,可语言尚未成型,故莫可名状。诗僧寒山子有诗云: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31】
所描摹的正是此间之情状。然而寒山子辈多半胶执于此,以为是至高境界—— “ 言语道断 ” 。殊不知,他们还只是停留于开端的懵懂处。虽然语言将出未出,但其势必兴,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如何言说迷蒙之境,而不是以停滞、审美之姿来拒绝语言。
“ 取譬 ” 本是为了语言的整体显现,是为了语言的敞开。所以,当人物相遭遇,语言将兴未兴之际, “ 取譬 ” 就显得极为重要。因为 “ 取譬 ” ,语言便不会滞塞于初生之机,反能得以持续而又整体的发生。所以孔子才会强调说:“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但孔子并未在此意义上直接使用 “ 取譬 ” 一词。语言兴起,并 “ 无达诂 ” ,孔子替之以 “ 诗之兴 ” 。《泰伯》云:“ 兴于诗。” 《阳货》云:“ 诗可以兴。” 孔安国以 “ 引譬连类 ” 【32】为释,是为得之。所以在《八佾》中,当子夏因 “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 而知 “ 礼后乎 ” 时,孔子极为赞叹,谓其 “ 始可与言《诗》已矣 ” 。《学而》篇中,子贡因与孔子论贫富之所当履而知《诗》 “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 之意,因果正与子夏相反,然孔子亦称 “ 始可与言《诗》已矣 ” 。两者的本质均在于 “ 引譬连类 ” ,故孔子云:“ 告诸往而知来者 ” 。“ 往来 ” 所云者,即语言发生之前际与后际被归拢于 “ 取譬 ” ,呈现为既能不忘其本又能朝向于未来的持存无间。故《诗·抑》云:“ 取譬不远,昊天不忒。” 安乐哲对 “ 取譬 ” 的理解正与此相似,他说:“ 譬比既取自历史人物文化成就的权威,又靠的是当下新环境的创造 ” 【33】。
如上,在语言实践中, “ 慎言 ” 与 “ 取譬 ” 恰如阴阳之相偶相成。“ 慎言 ” 若阴,收拢并警醒着语言归之于德,深根固蒂,使语言不至于违背其本性,发生异化。“ 慎言 ” 的实践,实质上彰显的是物之德。《易》云:“ 可不慎乎 ” ;“ 取譬 ” 似阳,专于生发,积极护送着语言从其根底——德——兴发,充周于世界。如此,语言便可无有窒碍地顺遂发生。“ 取譬 ” 的实践,彰显的是物之流转以及人物之间的感通,最终联结整个世界。故《系辞》云: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34】
两者相成,语言即德言的使命便真正达成。德性充满、洋溢,万物一体之仁全体展露。
三、语言隐退:无言
语言纯熟,德体既立,语言便不再停留于语言,将隐退以藏诸物用之下。子曰:“ 显诸仁,藏诸用。” 张载谓:“ 德其体,道其用。” 【35】于是物既在德性世界中凸显,却又不受困于语言;于是智周万物,大化流行,于穆不已。船山曰:
盈前而皆道,则终日而皆德,敦化者敦厚以化成也。【36】
语言隐退即 “ 无言 ” 之流行。“ 无言 ” 不与语言相对。它不是刻意沉默不说,也不是语言否塞不通;不是对语言的否定,也不是见到某境而顿然忘言;不是不可说,也不是语言所不到处。……一言以蔽之, “ 无言 ” 不是消极,它不是任何的不是,它是一切是的是。后世硕儒或许只有船山认识到这一点,故其谓:“ 论至此而微矣。非老氏‘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说也,非释氏‘言语道断,心行路绝’之说也 ” 【37】。又云:“ 夫繇言而知其所以言,与不繇言而知其所以言,是孰难而孰易?” 【38】
我们尚需看看孔子自己究竟如何看待 “ 无言 ” 。《阳货》篇记录了孔子和子贡关于 “ 无言 ” 的经典对话。当然,与其说是对话,毋宁说是语言与无言之间的亲密运作。且看:
子曰:“ 予欲无言。” 子贡曰:“ 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39】
子贡在 “ 孔门十哲 ” 中被归为 “ 言语 ” 科,对语言浸润之深可想而知。只不过心性使然,仍停留于语言之中不得而出。是故,孔子说 “ 予欲无言 ” 正是为接引子贡,欲其知晓语言必让出自身以归之 “ 无言 ” 。然子贡初闻,极为惊怖,故急应道:“ 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上文已述,圣人之言即德言,是为语言之根本。孔子不自称圣人,然在子贡眼里,孔子是 “ 天纵之将圣 ” 。倘若圣人不言,是谓语言无根。语言便无法兴起,后述者亦无以为继,世界更无从建立,或者即便建立亦将崩塌。故有子贡急迫之问。
至此,孔子已将子贡带入语言之机中,于是顺其势而问曰:“ 天何言哉?” 不论取譬于任何物事,均会有偏有倚,故孔子取譬于 “ 天 ” ,正是取譬于不偏不倚,取譬于大化流行,取譬于太虚氤氲。作为孔门精英,子贡完全知道取譬于天的意义与分量,然而 “ 天之所以为天者不言也 ”【40】。此问一出,原本被语言包裹且充实着的子贡,由原本的惊怖转而为惶恐:若不停留于语言,人与物将何处安置?
所以孔子继之曰:“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语言只是呈现充实光辉的德性,只是让物向人如实呈现,只是人物之间的相互照看。而 “ 无言 ” 所敞开的却是行动。行动有三重指向。
第一,是指成德行动——成己。人之所以为人,其首要任务即是成德。必成德而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行动主体。成德,即将天所赋命于我之性充实而光辉:滤尽渣滓,精粹充周,最终又返还于太虚之天,所谓 “ 成全而归之 ” 。行道有得于己谓之德,《孟子》曰:“ 有诸己之谓信 ” 。是故孔子始终强调 “ 言忠信 ” ,两相对照,德、信、言三者同一。是以上文所论 “ 正名 ” 之正,其实是指此成德之行动。是故《子路》云:“ 正其身,不令而行。” 必如此,然后方能有言。《里仁》曰:“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又《子路》曰:“ 子曰:“ 刚、毅、木、讷近仁。” 以至于孔子对归属于 “ 德行 ” 科的颜回、仲弓极为赞叹。而对子贡,孔子会教导说:“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 。子贡毕竟还是彬彬君子、 “ 瑚琏之器 ” ,依旧可造。然而对与子贡同属 “ 言语 ” 科的宰我,孔子明显没那么客气。起初既已给出警告:“ 听其言而观其行。” 可宰我却行有不逮,《里仁》云:“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 。然而宰我却如 “ 朽木粪土 ” ,毕竟无根,终究落于浮华、谄媚之中。是以,其后孔子便激烈怒斥:“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 。由此足见成德行动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是故《系辞》曰:“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德行——无言,却是语言的根据。
第二,是成物行动。船山曰:“ 天命之物者为物之性。” 【41】然物初与人无涉,茫然无迹。必当人物相遭遇而兴起语言之后,其性方显。然而语言只能让物如是呈现,却不能尽物之变,不能尽物之变则不足以 “ 育物 ” 。换言之,仅凭语言尚不足以尽物,此时需行动登场, “ 因用之以尽物理 ” 【42】,继语言以成物性,故船山云:“ 随其言而成 ” 【43】。语言召唤着行动,期许持续的行动将语言世界的光明呈现转换为行动世界的周流无碍。成物——无言,却让语言知周万物。
第三,是天道行动——天行。“ 天行不可知 ” ,这并非不可知论,而是因为天行远远超出人言与人行,语言无法企及。语言只在语言中发生意义,所以语言应当谨守自身,船山曰:“ 于道则默,于物则言 ” 【44】。孔子认为子贡最大的问题正在于 “ 不受命 ” ,喜用 “ 亿 ” 。朱子《集注》云:“ 亿,意度也。” 即是说子贡不安分,喜欢私意揣度,却 “ 亿则屡中 ” 。以至于孔子无可奈何地悲叹道:“ 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也。” 在孔子看来,子贡之 “ 屡中 ” 正是其不幸处。天行之下,语言当 “ 慎密而不出 ” ,不得以幸妄之言来强测天意。如此,无言则不妄,不妄即是诚,诚即是天行,天行于是 “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 ,万物如其所是地流行。天行——无言,却让语言极尽其诚。
语言隐退——无言,整个宇宙成为德性的恒久行动,生生不息,流转不已。《诗》云:“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张载曰:
大德敦化,然后仁智一,而圣人之事备。【45】
然而对话至此,便已结束了吗?显然不是。最后孔子突然又重复了一句:“ 天何言哉!” 此真为翻身天外之语。《诗》云:“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神妙不测,至矣!尽矣!无言之中,存神以观化,修德以体天。最终,语言又从原本的隐秘中再度闪现,只为 “ 赞天地之化育 ” !
一层一层,循循善诱,足见孔子语言之精妙,亦见其语言实践之纯熟。是故颜回赞叹孔子,云: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46】
孰谓孔子 “ 不贵言 ” 【47】也哉?
注释:
[1] 陆象山语,其云:“《论语》中多有无头柄底说话”。参见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95页。
[2]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53页。
[3]彭传华:《孔子语言哲学思想探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38-44页。
[4] 此说发皇于郑玄、皇侃,以为“正名”是因“孔子见时教之不行,欲正其文字之误”。曾流行于清儒考据诸家。
[5]此说倡自司马迁,其后程朱继之,进而影响理学。
[6]此说为马融之观点,近人程树德从之,并疏之云:“当今所谓伦理学也”。
[7] 其实早在明末清初之时,李文藻以《名理探》来翻译波菲利所撰的通俗读本《亚里士多德范畴概要》时,便已有将“名”当成概念的趋势。至冯友兰将此挑明之后,至今仍在此阴影之中,如柏拉图派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派的解释、语言哲学派的解释、还原主义派的解释等等。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页。
[9] 温海明《“名”出“言”,以“言”“行”事”——孔子与庄子意义观之比较》,《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59-65页。
[10]陈启云《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128页。
[11] 赵炎锋《先秦名家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12]陈汉生《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13]邓晓芒在其《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比较》一文中,认为孔子的言说方式是一种“权力话语”,必然“导致话语权威”。参见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163页。
[1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65页。
[1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81页。
[16]徐复观在其《名的起源问题》一文中,将诸子对命名依据的争论归结为以荀子为代表的“现实派”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理想派”,但他在立场上更同意荀子。参见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17]陈启云《: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第127页。
[18] 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第316页。
[19] 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第316页。
[20] 马一浮《复性书院讲演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21]《礼记正义》,郑玄注,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4页。
[22]龚建平亦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要看到德与言的统一”。与本文观点不同的是他又强调“德”与“言”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发现“德”是“言”的根据。参见龚建平:《德与言——孔子儒家言说方式刍议》,《人文论丛》2004年卷,第57-64页。龚建平:《儒家的德性语言观》,《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20-23页。张刚认为,“语言的价值不只是传达言者的思想,而在展现言者的德性。”在其具体的论述中,有将言与德对等的意图。参见张刚:《德与言——儒家语言观研究》《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第22-27页。
[23]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抗,盛冬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版,第361页。
[2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7页。
[2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2页。
[26] “躁”即“懆”,《说文》曰:“愁不安也”。不安者,不安于其位也。
[27] 庄子:《庄子注疏》,郭象注,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4页。
[28] 陆德明:《经典释文》,张一弓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02页。
[29] 王琼言:《双溪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30] 以上所论,乃郭象、陆德明辈之理解,不一定就是庄子原意,这本不在本题讨论之内。然而,庄子对语言本持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却为大部分研究者所公认。参见徐克谦:《论庄子的语言怀疑论》,《现代哲学》2006年第1期,第103-107页。
[31] 寒山:《寒山诗注》,项楚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页。
[32] 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9页。
[33] 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第354页。
[34]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潘雨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86页。
[35] 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页。
[36]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70页。
[37]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第870页。
[38]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第869页。
[3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0页。
[40]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第869页。
[41]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第457页。
[42]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091页。
[43]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第405页。
[44]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第405页。
[45] 张载《张载集》,第18页。
[4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1-112页。
[47] 朱子释子贡“亿则屡中”时,引范祖禹之言,谓:“圣人之不贵言也如是”。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