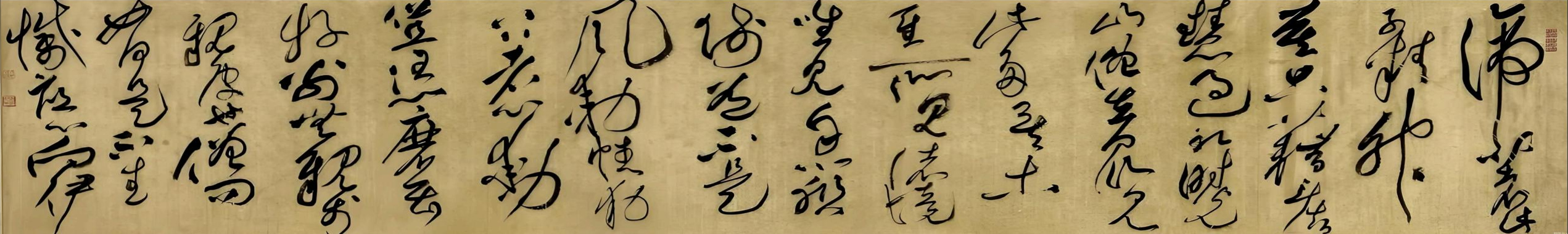民间文化视野下国创动漫中母亲形象的建构——以哪吒的五版动漫故事为例
张 琰 王 敏
【内容提要】文章以民间文化视角切入,考察1979年至2019年间五部哪吒题材动漫作品中哪吒之母形象跟随时代变化的建构轨迹。从《哪吒闹海》到《封神榜传奇》,母亲形象的由虚到实隐含着民众对安定与达观的精神追求;《哪吒传奇》与《我是哪吒》以女娲和莲花类比母亲,传达出民众推崇母性与实用之美的观念;《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母亲形象走下神坛,其显示的民间文化元素照应着现实,透射出人情人性美与真实感。文章认为母亲形象的变化展现了民间文化与流行文化的融合,这为国漫的创作带来了新思考。
【关 键 词】民间文化;母亲;哪吒题材动漫
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更多是一个空间概念,主要指以农村为主题的空间,本文所论述的“民间”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是“从人群体所处的社会角色、社会位置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历史价值等方面综合分析、考察而确立的” [1]。哪吒的原型最早出自印度古诗,而后渐渐传入中土,从宗教圣坛转向民间世俗。在宋代时“哪吒”形象已有“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描绘,《五灯会元》卷二中有记载:“那[哪]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现本身,运大神力,为父母说法。 ”[2]随后在宋元之际流传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对哪吒及其传说进行了更为丰满的表述,成为此后明清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哪吒故事的蓝本。哪吒故事在通俗小说中的演变从侧面展现着民间受众对哪吒及李靖夫妇形象的接受与认知,而随着我国影视行业的发展,哪吒故事被多次引入荧屏。在媒体镜像的投射下,哪吒和其父母被罩上流行文化的光晕。民间文化与流行文化的交织与碰撞使得哪吒故事被赋予新的精神内涵,其中的母亲形象也随时代与具体的故事背景的转变而变化。于民间文化立场之下,从其变化过程可窥看出人物身上折射出的民间精神指向。
本文将 1979年《哪吒闹海》、1999年《封神榜传奇》、2003年《哪吒传奇》、2016年《我是哪吒》、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这五部动漫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依据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母性特点与民间文化内蕴分为四类,从具体的文本中分析哪吒母子的伦理关系,探究母亲形象是如何被建构的。
一、《哪吒闹海》:虚化的母亲形象
《哪吒闹海》是 1979年在国内上映的首部关于哪吒故事的动画电影,其取材于古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影片中哪吒因闹海伤龙而得罪龙王,在父亲和龙王的双重压迫下“剔骨还父,削肉还母”,最终在太乙真人的协助下获得重生,击败了为害一方的恶龙势力。在带有强烈的反叛伦常、抗争强权的斗争精神之情节设置中,哪吒之母的形象是近乎透明的。她不承担叙事层面的实际功能,成为了闹海反父传说的背景性存在。
母亲的虚化呈现与该部动漫的情节安排关联紧密。在《封神演义》小说中,哪吒之母与李靖是一体的角色设定,在闻知哪吒得罪东海龙王之后无不怨怒地指责自己的儿子,将孝道紧紧地捆绑在哪吒身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伦理联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道德胁迫。哪吒之母是以李靖为代表的父权压迫的帮凶,故而哪吒随后以自残的形式终结了与父母双方“骨肉之亲”的联系。而在《哪吒闹海》中母亲形象从始至终没有正面出现过,“母亲”在闹海的整体叙事中成了一个仅有亲属代称的概念意义的符号。哪吒反抗的强权由脸谱化的恶龙顶位,反叛的父权也局限于李靖这一单独的形象,哪吒“削肉还母”的对象消失了,其内心无尽的不甘与叛逆只得指向父亲一人:“爹爹,我不连累你,我把骨肉还给你。”缺少母亲具体形象的支撑,哪吒反叛的孝道与家庭伦理似乎也成为了父子之间单调的冲突与对决。在此,母亲的虚化处理是否在文化意义上有着独特的作用呢?
首先应当承认的是,无论在民间文化还是精英或者大众文化视野之下,母亲都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类肉体的出处与精神的归处。母亲身上独具的母性是每一个人类成员曾赖以成长的精神依托。而《哪吒闹海》中极为紧凑的情节与有着明确矛盾站位的角色安排无意于对母亲的形象进行设定,这意味着母亲在整场的反叛斗争中形象是虚化的,于血雨腥风的抗争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该作品将温情慈爱的母亲从残酷黑暗的权力角逐场中剥离出来,文本的设置一则保持了国民对母亲温和包容、护子舐犊的传统形象的认知,二则避免了母亲站位何方的尴尬局面。哪吒对父亲的单向性“骨肉归还”似乎模糊地暗示着隐形的母亲对儿子的行径是持“默许”态度的,这种无言的支持恰是对母亲形象虚无定型的反向补充,以沉默、虚位的存在形式同儿子建立起无可指摘的精神关联,呼应着民众视野之下骨肉相连、母子情深的亲情期待,也为父子反目、悖伦叛逆的抗争叙事点上一笔隐藏的“希望”。无论文本结构之下的母亲预设是何种状况,在《哪吒闹海》中母亲形象的缺失实则维护住了其对孩童而言的庇护者与安抚者的形象认知,保留住了半遮面的神话中仅存的亲情温度。这实则符合民众在传统观念中对母性与母亲的信任与依赖。对渴望母性的想象性表达是民间文化中“达观”的隐性吁求,即抛却了功利性的追逐与对抗,向以温情为代表的宁静、祥和的精神回归。就一定意义而言,这也为哪吒题材的动漫创作打下了人物塑造的基本性格底色,留下了哪吒之母形象创造的扩充空间,亦为其他国漫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塑造提供了启发意义。
二 、《封神榜传奇》:实体化的母亲形象
“持有民间文化立场的当代文学创作对‘善美一体’伦理价值观的主张,其实质也是普通老百姓审美观在文本中的一种反映”,这“是民间普通群众看待人际相处之道的群体性心理积淀,认为善的就是美的,而不必过度计较是否符合生活的真实逻辑” [3]。在这种善美一体的伦理价值中,对外物自在恬淡、生活上超脱闲逸,于功利不争不抢的达观心态也是此种善美一体伦理价值的重要体现之一。《封神榜传奇》首次出现了哪吒母亲的形象,与原著《封神演义》和《哪吒闹海》相比,母亲形象的变化与主人公哪吒成长修炼环境的清净闲适值得我们关注,二者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相互映照的关系。
《封神榜传奇》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于 1999年制作的 100集电视动画片,故事与《封神演义》中武王伐纣的历史背景一致。但其中的君民冲突与阶级对立被大大削弱,以哪吒为代表的青年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成为了情节推进的主要元素。在哪吒与东海结下误会的情况之下(龙王不是反面角色),龙王意欲水淹陈塘关
以逼迫李靖交出哪吒,李靖夫妇平日对哪吒十分疼爱因而拒不放人,在危机之下哪吒甘愿以自己的性命交换陈塘关的安宁。在此情节之中,“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反叛抗争意识彻底消退,父子之间的矛盾斗争不复存在,在人物关系的组建中没有明显的矛盾对抗,唯一的冲突竟来自于参与者的误解。当误会解开时哪吒的牺牲反而无法彰显出观众心中设想的价值与意义了。于是主角牺牲的崇高感被降低,随之而来的复活情节也理所当然地出现,但哪吒重生之后却失忆了,失忆成为情节的一大突转。
哪吒的失忆准确地指对于李靖夫妇:“我只记得有师父,不记得有父母。”哪吒重生之后便潜居于太乙真人的仙境中,与自然万物为伍,远离尘世喧嚣,不问世间百态。重生后的生活宁静而闲逸,这一宁静生活的时段恰好是婴孩刚刚出世之后静躺在襁褓内生活的补位。在哪吒重生的意识中,他舍弃了生前的争斗与恩怨,自己生于自然,长于自然,无拘无束、悠然自得,视养育万物的天地自然为母。这里看似是对母亲的忽视与淡漠,实则是将人母与“地母”视为一体。“母亲”构成的多位性是哪吒对达观精神的正面追求。这部作品中哪吒之母对儿子非常关心,但情节的设定无法令母亲将舐犊之情淋漓体现,于是在哪吒重生之后,故事以更为宏大的视角弥补了哪吒从“肉球”到小英雄中间的成长历程——是符合常人在婴孩时代该享有的宁静、恬淡与安全。“人母”与“地母”是异形同质体,二者互相映照,“人母”在形象上具备母亲应有的具象化外在特征,而“地母”则承担着母亲对哪吒应有的可信任与可依赖的作用。哪吒对自然之母的认可,是其对达观精神的正面呼求;“地母”的补位是对本部动漫作品呈现出的闲逸达观心态的一个具体的呈现,这也传达出《封神榜传奇》在整体的叙事中流露出的达观精神与超脱情致。
三、《哪吒传奇》与《我是哪吒》:具象类比下的母亲形象
(一)《哪吒传奇》——女娲:神化的母性力量
女娲造人与补天的神话在民间广为流传,民间对女娲事迹的流传形式一则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二则是通过画像砖、帛画、壁画等介质完成对母神的歌功颂德。唐宋以后,民间便有女娲祭祀的活动,《癸巳存稿》卷十一记载:“宋以前正月二十三为天穿节,言女娲以是补天,俗以煎饼置屋上,名曰补天穿。”[4]女娲由神话传说演变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在民间文化中,女娲被视为集救世、造人、生育、婚娶等多位崇拜功能为一体的“大母神” [5],对女娲可以庇佑苍生、送子福荫的传统观念烙刻在民众的集体意识中,从而形成了对女娲这一母性神 [6]的信仰与敬畏。
突出成长与奉献主题的《哪吒传奇》呈现出典型的英雄历险故事的情节发展特征,在哪吒协助武王伐纣、斗争妖魔的过程中,除却主人公哪吒被创作者有意地聚焦特写,女娲这一人物形象也备受关注,其在哪吒系列动漫作品中首次被放诸于情节发展的核心范围,并与哪吒的生母殷夫人共同成为了哪吒故事叙事的施动者。故而本片中“母亲”的功能和意义由殷夫人与女娲共同承担,二者具备这样的互指关系:女娲被人类视作“全能”的大母神,而哪吒的母亲对待哪吒便如同人格化的女娲对待缩小的人类群体,赋予其生命,并指引其如何生活与发展。本片具体情节中也呈现出这样关系:哪吒之母总会对哪吒讲女娲造人的故事,温和慈爱的语调以及故事内容的呈现,实则是自己对哪吒以及女娲对人类的相互映照。而哪吒在委屈时无法向生母哭诉便想找女娲娘娘评理。在其内心深处女娲是世间最宏大崇高的母爱集合体,当自己缺乏母性关怀时,自然地向其寻求心理的补偿。因此女娲与哪吒之母共同属于“母亲”的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哪吒的母亲是女娲所代表的母性力量的具体延伸,而女娲是前者的宏大化呈现。
两位“母亲”在哪吒成长的整个事件集合序列中,共同作为叙事的推动力量贯穿首尾。第一,“母亲”在叙事结构中是启动哪吒反抗暴政、斗争邪恶的发起者。女娲借降服石矶之事第一次令哪吒有了使命的背负与认知自我和世界的机会,她是推动哪吒迈出英雄之步的第一个推手;而哪吒的生母则在哪吒遇到艰难的抉择时洞悉他的真实想法,排除其疑虑,坚定地支持他助周剿纣。哪吒的生母是推动哪吒不断成为“英雄哪吒”的第二个推手。第二,“母亲”是哪吒在成长途中完成重大转折的助力者。哪吒自杀后在女娲的帮助下死而复生,重生的哪吒带着对自我与世界的新认知继续前进,这是哪吒的首次转变。第二次转变是在同石矶的最后决战中,哪吒丧失心智,其生母作为情感的“软性力量”,用慈爱唤醒哪吒;女娲作为法力的“硬性力量”,用神力帮助哪吒战胜石矶、走出玲珑塔。在少年英雄的整个成长叙事中,“母亲”始终作为施动者,帮助哪吒最终成长为真正的英雄。
母亲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除却以具体生动的凡间人物呈现,也兼之以具象化的女神作为类比、补充说明,将母性力量神化,予以母亲形象地位以升格的形式处理,再现了民间文化中的母性崇拜与女神信仰。母亲被赋予母神身上具备的创造生命、信念寄托以及精神皈依的光晕,将神性的力量转嫁于现实的人物身上,以达成民众寻找自我精神归处和安慰的心愿,从而在日常中获得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此外,哪吒从母亲与女娲处获得两次重生的力量,这两次的重生情节一次是情节的突转,另一次是全剧的高潮,可以说本部作品全部的情节演进均与母亲的力量密不可分;而展现母亲力量在作品中最频繁的形式便是生命的诞生或重塑——紧紧与生殖相关,这是民间传统文化中对母性的尊崇与生殖崇拜观念的最直接的体现。剧中出现的母亲救子的情节与传统观念中对母爱伟大、无私、包容特点的认知相和,延续了母子伦理间的母慈子孝的传统认知,顺应了民众对母亲、母性的既成观点。
相较于《哪吒闹海》与《封神榜传奇》,母亲形象在《哪吒传奇》中的呈现将母性的力量推至神坛,这种对民间较为原始的母性崇拜观念的再现并非是单纯意义上的“返古”,实则是将母性推崇与直观化、夸张化、浪漫化的动漫演绎形式相对接后,产生的一种“返古照今”的文化用意:随着个体家庭在社会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亲子关系与家庭和谐被愈渐重视。如何在信息化、现代化的当今环境之下为逐渐生活“孤岛化” [7]的 90后子女们及时地做出孝亲、亲亲的正面引导,民间传说中哪吒的事迹为之提供了可改造、可运用的故事空间。以生动、炫目的动漫为媒介,将民间传统文化中母性尊崇元素化之为当今环境下尊母、孝亲的观念引导,也获得了受众的一致认可,这是将民间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成功对接的一次范例。
(二)《我是哪吒》——莲花:实用之美与望子成龙的联系
《我是哪吒》讲述的是神仙太乙真人授艺于哪吒、龙女、土行孙三人,共同对抗东海夜叉与龙太子、维护海陆和平的故事。与《哪吒传奇》相比,于 2016年上映的《我是哪吒》中母亲在故事里所占的分量并不多,创作者将母亲与一具体的物象睡莲相关联,它作为母性力量的符号穿插在哪吒成长的叙事中。
莲花或者荷花在我国形成了历史悠久的荷莲文化传统。在文人文化圈中,莲象征着高洁品格与宁静淡泊的心境;在民间文化中,莲象征着和合与吉祥:“莲又称荷,与‘和’谐音。民间吉祥画,‘和合二仙’,便是一人手中持荷,一人捧盒,以示和合。”“中国画以荷花、海棠、飞燕构成一幅图,谓之‘何 (荷 )清海宴 (燕 )’,喻天下太平。以莲花和鱼剪纸成图张贴,谓之‘连年有余’,表示富足有余。许多与莲有关的话语,莲子代表连生贵子,藕为佳偶。”[8]可以看出,民众对莲花的喜爱不以其形与色为由,也不将其与人格品行相关,而是将莲花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相关联。这种以其对生活有益或是产生实用之功来作为对某一事物喜恶的标准体现了民间文化立场之下实用之美的价值取向。
《我是哪吒》中的少年哪吒虽生性顽劣,却心怀大志,“知子莫若母”的殷夫人力排众议,始终认为其子必将如淤泥中的睡莲一般,虽晚开却终得盛放。含苞待放的睡莲一是具有情节设定的指向性功能:意指花开晚时,哪吒大器晚成,良马遇伯乐方可驰骋四方;二是人物内心情感的外向流露与寄托:莲瓣包裹莲台,莲子被护在心中,哪吒之母的宽容、慈爱与守护期待尽显莲苞之内,温情的包绕正代表殷夫人的舐犊之情;三是“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民间情感寓意:莲子与“怜子”谐音,而哪吒之母将睡莲晚开与哪吒大器晚成相关联,其正是中国百姓对子女所存有的最为常见的期待心理。莲花在此不似文人笔墨之下对美人的“芙蓉容颜”的物拟以及对君子洁身自好的品行寄托,其被创作者从颜、德的外在审美和品格批评的高雅领域摘取回民间场域的百家烟火中,从而获得了沾染民俗气与人情味的俗世之美。
《我是哪吒》中的小英雄虽天生神力却具备争强好胜、顽皮倔强、冲动莽撞等现实生活中普通孩子的缺点,从这部动漫作品开始,哪吒作为少年英雄的形象塑造“底本”便开始接近平凡生活,与之相对应的母亲形象亦渐渐显露出普众家庭中母亲具备的特点,诸如引导教育孩子、对顽童心性仁慈而宽厚等性格特征。睡莲物象与母爱母性的互指互证让民众对莲花的实用之美的审美倾向与生活中母亲对子女的现实期盼相关联,贯穿首尾的具象化母爱作为母性符号的凝固体,传达出民间视野之下百姓对“母亲”最为朴素与直观的体认与想象。
四、《哪吒之魔童降世》——“落地”的母亲形象
《哪吒之魔童降世》(下称“《魔童》 ”)讲述的是:因命运错位,哪吒生而为魔丸,龙王之子敖丙生而为灵珠,二者机缘之下成为好友,但因各自的身份问题而卷入了人、妖、神三界的矛盾争斗中,最终二人共同承受了天雷劫,并在生死考验中坚守了命运应由自我书写的信条。《魔童》的人物设定与情节安排相较于前四部动漫作品而言,离封神故事的原文化语境最远。这其中哪吒闹海的桥段虽未减,但却并未有意凸显对权力的抗争,聚焦视角从历史拉向当代,人、妖、神之间争斗的核心指向实则是现实社会环境下人对身份问题的焦虑与精神撕扯;与此同时,其中哪吒之母的形象也是在这五部动漫作品中最为接近现实生活、充满人情味与“民间气息”的母亲形象。哪吒母亲的形象在本部作品中真正地“落地”了。
“落地”的母亲形象在一众深陷身份困惑问题的各类人物中显得尤为独立:神的身份焦虑——志在神位却不得师门信任的申公豹;妖的身份尴尬——希求天界认可却被囚于海底的龙族;人的身份疑虑——错投魔丸、百夫所指的哪吒与情法相悖、无可取舍的李靖。在《魔童》的人物群像中,哪吒之母虽戏份不多,却是唯一不受身份困惑的女性角色。同为魔童的直系亲属,哪吒之母相较于李靖却更无身份桎梏,精神独立洒脱。其一是仪容言行等外在层面的自由独立性。殷夫人含胎之时并不似传统官宦妻属闭于内室、高卧绣榻,而是挣开丈夫搀扶的手臂,左手握饼右手持肉而大快朵颐,信步熙攘的民巷;在神庙之中,丈夫恭敬肃然而拜,殷夫人却挺腹长立,公然斥责神龛的无用;在分娩之时,李靖尚在犹豫打醒醉酒的仙官是否有失斯文,而殷夫人却将阵痛的战栗毫无遮拦地以粗话宣泄出来,哪吒之母的率性而为与李靖的恪守礼规,二者动静相衬、一明一暗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丈夫的持重守礼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官庙文化,那么殷夫人的“返璞归真”则较大程度还原了民间尘土气息之下平凡民妇的生活状态。
其二,奔放自由的举止背后凝聚着民间文化中落于实处、归于自然的审美价值取向,也传达出创作者对民众真实质朴的人情人性美之肯定。勤劳持家的百姓终年在烟尘荡涤下奔波劳碌,生活之美也与其所看重之物的可用性、实在性紧密相关。女娲或其他神像的供奉必然连接着百姓对其可有“实用”的心理期待,当其功用未落于实处,神性的谎言便被民众戳破——举止泼辣、言语带有俚俗气息的殷夫人怒砸女娲像“拜了三年还不生,再不灵验我砸了这破庙”。大母神的推翻既反映当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行为影响力的提升,也是民间文化中鲜活生命力与生活感的重要体现。在过去,对女神的崇拜是群众集体未脱离精神依托并依旧带有对传统文化中迷信成分的依赖的体现。而将女神拉下神坛,打破了母性神话与虚假的精神安慰,将一个真实、鲜活的母亲归还自然与本真,允许母亲身上彰显出自身的脾性特点,是对母亲回归现实、释放女性在家庭中真实自然的本性的认可与对母亲的真实人性、质朴情感的关照。
此外,作为神话故事改编作品的《魔童》,其中的母亲形象较为罕见地与孩子形象站在了“同一高度”上。此剧中母子游戏桥段的设置恰好将哪吒与殷夫人性格泼辣、脾气倔强的特点对应起来,并在哪吒闯祸后有意地插入母亲进行自我检讨的情节,此时的母子身份不存在悬差,祸事和反省并存的情景是在将人物拉近现实生活,反照当代家庭亲子问题。而传统民间故事中的救母传说虽并不少见,然桃山救母、沉香救母、目连救母以及水浒故事中的李逵杀虎报母仇等故事皆传达出了母子之间复杂的位置关系:无论为母者生前善恶与否,她皆成为验证子辈是否真正孝义善勇的“试探之物”,即无论“母亲”的人格与身份处于何种状态,高低贵贱均无法成为阻碍母亲横轧子代的合理借口。母亲与孩子之间虽有亲敬之情却悬隔着辈分与伦理的差异认知。但此种隔阂随着个体家庭在社会中地位的日渐凸显而有所弥合,从《小蝌蚪找妈妈》中青蛙母亲被作为子代的追随者、依恋者形象呈现;到《宝莲灯》中天仙母亲始终与沉香的信念投射物“宝莲灯”相关联,其实母亲扮演的是子代的理想指引与精神庇佑者的角色;再到哪吒系列动漫作品的改编重构,母亲的形象渐渐从伟大、高远、柔美的地位“悬浮者”蜕变为具备性格特殊性、沾染烟火气的普通人。这回应了时代不断前进、民众对自我以及万物的认知水平不断提升的实际状况,也将民间文化元素的传递从传统拉向当下,照应了古与今相协调、创作和现实需求相结合的理念。
五、动漫与民间文化的对接
动漫是一种流行文化的形式,民间文化中的母子伦理关系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积淀,民间文化中的传统观念在与流行文化嫁接之后,并未显得十分突兀与不协调,反而在相互交织中使得彼此双方均实现了价值增值,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一种新的母亲形象价值认同的传递。这对于文艺工作者在思考如何赋予民间文化新的生命活力与充实流行文化的内涵要素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哪吒母亲的形象在这五部动漫作品中经历了从隐形到显形,由虚到实,从神性化到人性化的过程。从无到有,从模糊到具体的演变是动漫文化对母亲、母性问题的关注;母亲形象背后透露出的民众达观精神追求与现实生动的人情人性特点则是动漫对民间文化中百姓群众的审美倾向与价值追求的捕捉。将民间视域下的审美、文化和伦理价值与动漫的艺术呈现形式相对接,使得民间文化拥有了新的演绎窗口,亦使得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获得了内涵补充。
王光东指出:“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强调‘民间’是有意义的,中国的民间社会并不是一个虚幻的空间,而是有其相对独立的运转系统,不仅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内容,而且对于当代人精神的生成和真正中国化的现代性作品的出现都有着重要意义。”[9]哪吒的原型人物来自外域的宗教,但经我国民间土壤的培植,哪吒这一人物形象经过百姓生活环境与民俗文化的熏陶、糅入文人创作的审美想象与精神意志,迸发出普通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浪漫色彩与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性感悟与思想批判的火花。民间的场域为文艺工作者提供着朴素真实的素材与对精英文化及其自身反思和关照的对象,通过深入民间文化的探寻,创作者们可以获得对自我想象力的激发,创造出贴近现实与普通民众的人物形象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就民间神话与传说中蕴含的想象而言,“它一方面与民间的底层社会有关系,另一方面又对抗现实,依靠想象完成有希望的人生,浸透着浓郁的审美化人生精神,具体在民间文学中就是人、神、鬼以及动、植物可以相通相生,人间、地狱、天堂可以自由来往,呈现出圆融博大的想象空间” [10]。母亲角色从 1979年到 2019年,其在哪吒系列动漫中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从人物形象单薄扁平到角色的立体丰润,形象的变化与叙事情节的转换相辅相成。哪吒故事一路变迁却焕发出勃勃生机,正体现着民间文化要素本身具备的深厚底蕴与顽强生命力。
相较于它类影视呈现方式,视觉、听觉效果更具直观性与夸张化的动漫是吸引低龄或年轻化受众的一个重要的流行文化传播媒介。而其受众所具有的年轻化特性决定着动漫作品在内容上呈现出对时代潮流的顺应性,在形式上展现出对声、光、色运用的复合性与多边性。这些特点可以在短期之内博得大众的支持与追捧,然而精神蕴藉与文化内涵是文艺作品的精髓,动漫等流行文化产品想要拥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仍需在艺术形式之下的文化内涵之中投注更多的心血。
将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基因植入新时代新潮流下的文化形式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建构出满足人民群众审美需求与精神启蒙的文艺发展局面。就动漫创作本身而言,对传统民间文化元素的调动运用使得国漫的发展进入了崛起阶段:《一人之下》中对民间地方性民歌小调的运用唤起了青年受众群体对民歌文化的关注,也为动漫本身招徕了众多漫迷的支持;《白蛇:缘起》在民间传说故事《白蛇传》的基础上加入对人与生态关系的反思,使得人妖不伦之恋中也具备了对当今时代生态伦理问题的思考;而哪吒系列动漫以闹海、伐纣等封神故事作为中心情节,跟随语境的变化赋予其全新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使得传统文化获得了在新时代言说自我的权力,也将当下问题借助民间传统故事的形式暴露出来,使得民众在获得审美体验的同时也能够作出对自我以及周身大环境的反省思忖。
结 语
哪吒母亲的形象在四十年间的嬗变历程中实则是一个不断吸收民间文化元素又对之进行扬弃的过程。哪吒之母形象呈现出一种不断朝向真实性、多面性、立体性的发展态势,是在民间立场之下对人物人情美、人性美的塑造与审美追求。而针对民间神话传说故事之中原本具有的糟粕,诸如迷信崇拜等进行改造与加工,使之成为具备民间风俗活动的特点但又不违背主流价值观的呈现方式。在这一扬弃的过程中,母亲的形象既具备着时代前进过程中民众的自主意识复苏与觉醒的痕迹,也拥有着关于母亲这一特定群体对自身身份的思考和追问。
将民间文化元素与流行文化形式相对接,使文艺工作者能够创作出更多符合人民群众审美倾向并具有精神启迪意义的文艺作品,使沉睡的民间文化元素被唤醒,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广为流传的形式之中,同时促进流行文化吸收更为厚重的文化元素,使之在长久的文艺发展历程中经久不衰、独具时代特色,这是值得我们努力的方向。
【注 释】
[1]杨少伟 .张艺谋电影作品的民间性 [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6): 51-53.
[2]普济 .五灯会元 [M].北京:中华书局, 1984:116.
[3]王敏 .当代文学创作中民间立场的价值重估 [J].当代作家评论, 2020(4): 75-81.
[4]张国华 .女娲形象研究 [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5]参见刘勤 .女神降格研究 [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根据艾利希 ·诺伊曼著、李以洪译的《大母神:原型分析》:“外在被经验为世界——身体——容器,一如一种被神话统觉经验为宇宙实存、神祗、星星的‘无意识内容’,被视为是在大女人的‘肚腹’里”的图式”,而后我国学者们将女娲、西王母等女神定格在大母神的位置上。
[6]参见刘勤 .女神降格研究 [D]。所谓“母性神”,就是指具有“母”的身份或者名号,其司职与生命、生殖相关的女神。
[7]王润平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中的文化传承问题 [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其认为独生子女受到同龄及祖辈的影响教育很少,他们陷入核心家庭中的孤寂天地,父母是孩子接触最多的人员,电视等电子媒介是孩子了解外界的主要渠道。
[8]万颖 .中国文化之莲花现象综观 [J].语文学刊, 2014(4): 69-84.
[9]王光东 .民间文化形态与八十年代小说 [J].文学评论, 2002(4): 164.
[10]王光东 .民间文学传统与“我们” [J].当代作家评论, 2012(2): 120.
*本文系201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士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 XJ2019G006)、自治区青年拔尖雪松计划、自治区天山英才二期项目的阶段成果。
张 琰: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王 敏: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自治区级基地新疆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喀什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